
資料來源:PC3
近來台灣不少人在私下談話中常會提到一句話:「等川普下台,一切就會回歸正常」在他們的想像裡,美國政府對半導體、人工智慧、能源等產業的強力介入,僅僅是川普個人任期內的政治手段,最終還是會回到「市場決定一切」的商業邏輯。這樣的期待雖然可以理解,但若從美國近年來的政策與結構性轉向觀察,這種想法其實過於樂觀,甚至可能導致企業誤判風險,本文將從 Intel 入股案、對輝達徵收中國營收稅,到台積電與美國戰略定位的關係,逐層解析美國科技戰略已經進入「制度化國安時代」,不再只是短期政治人物的選舉操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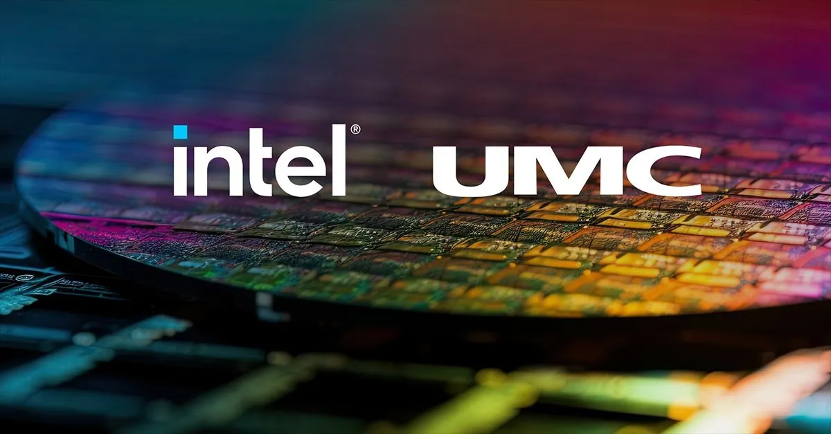
英特爾正在力挽狂瀾(資料來源:EDN Taiwan)
美國政府近年積極推動《CHIPS and Science Act》,意圖透過補助計畫吸引半導體製造回流。然而,對 Intel 的直接或間接入股,則標誌著一個更深層次的轉變:美國不再只滿足於「市場誘因」,而是開始以股權形式將企業嵌入國安體系。這樣的介入背後至少有三個考量。首先是戰略產能保障,美國要確保境內永遠存在可調度的先進製程能力,即使在台海或全球供應鏈受阻時,仍能維持軍事與 AI 晶片的供應。其次是技術自主與防外流,Intel 在先進封裝與 CPU 架構仍具優勢,國家入股意味著政府能在技術授權、海外合資上握有否決權。最後是制度化的戰時動員,Intel 的產能未來將不僅是商業資源,而是戰時基礎設施的一部分,如同能源儲備般可優先動員。這些發展代表 Intel 已不再只是市場參與者,而是「美國科技戰略的制度性支點」。
2025 年,華府對輝達課徵 15% 的「對中營收稅」,更是一個具有指標性的事件。它揭示了美國政府的政策工具,已從出口管制延伸到直接懲罰企業的市場依賴結構。對輝達來說,這項政策的影響有兩層:一方面是財務壓力,中國市場原本是其高端 AI 晶片的重要需求來源,課稅直接壓縮其利潤;另一方面是供應鏈轉向,為了符合美國政策要求,輝達被迫調整下單結構,更多考慮 Intel 或美國境內台積電廠的產能。更重要的是,這項政策對台積電也產生間接衝擊。由於台積電是輝達高端晶片的主要代工廠,當輝達被迫減少對中銷售、調整產能時,等於間接限制了台積電對美國以外市場的影響力,並加速「產能導流」至美國可控範圍。換言之,輝達事件不是孤立的,而是華府對外部資產(台積電)、中層資產(輝達)、內層資產(Intel)進行「分層管理」的制度性設計。
許多企業仍相信「川普下台後,政策就會放鬆」,但這種想法忽略了一個事實:美國對科技產業的介入,已經進入制度化階段,不再是單一政黨的短期政策,法律與預算已跨黨派鎖定,例如《CHIPS Act》、出口管制清單、國防授權法,都是跨黨派支持的法律,難以因政黨輪替而推翻。更重要的是,全球盟友也在同步行動,歐盟、日本、韓國都在推動類似的「供應鏈回流」政策,美國的策略是國際趨勢的一部分,而非孤立現象。再者,企業決策邏輯本身已經被「國安邏輯」重塑,例如投資回報不再只取決於市場,而是政策保障與戰略價值。這意味著,即使川普卸任,美國政權更迭,科技產業「國安化」的趨勢依舊會延續。
從 Intel 入股案到輝達課稅,再到台積電的戰略定位,我們可以看到更深層的戰略邏輯,美國正在重塑國家與企業的關係,從「市場領導國家」轉向「國家領導市場」,企業逐漸成為國安架構的一部分;同時,美國也在建立戰略產能儲備,把半導體視為「21 世紀的石油」,未來甚至可能出現「戰略晶片儲備」的制度。此外,科技企業不再只是商業單位,而可能在危機時被納入戰時生產鏈,而在國際層面,美國正透過企業行為輸出自身的安全規範,對抗中國推動的「華為–中芯模式」,形成技術標準之爭。這些發展都不是四年一任的政策,而是長期的制度工程。
對台灣企業來說,最大挑戰在於如何同時應付「美國制度化的科技管制」與「中國市場的現實依存」,這意味著,過去習慣在兩大市場間靈活操作的商業模式,將越來越難以維持,若繼續寄望於「川普下台後一切回歸正常」,便可能錯過提早調整的黃金時期,業者真正需要的是建立「雙軌佈局」:一方面在供應鏈、產品規劃上緊貼美國的戰略方向,確保能在政策誘導下持續獲得市場與資金支持;另一方面則必須謹慎管理在中國的曝險程度,避免在地緣政治惡化時成為被鎖定的風險對象。